抗戰八年,家人四散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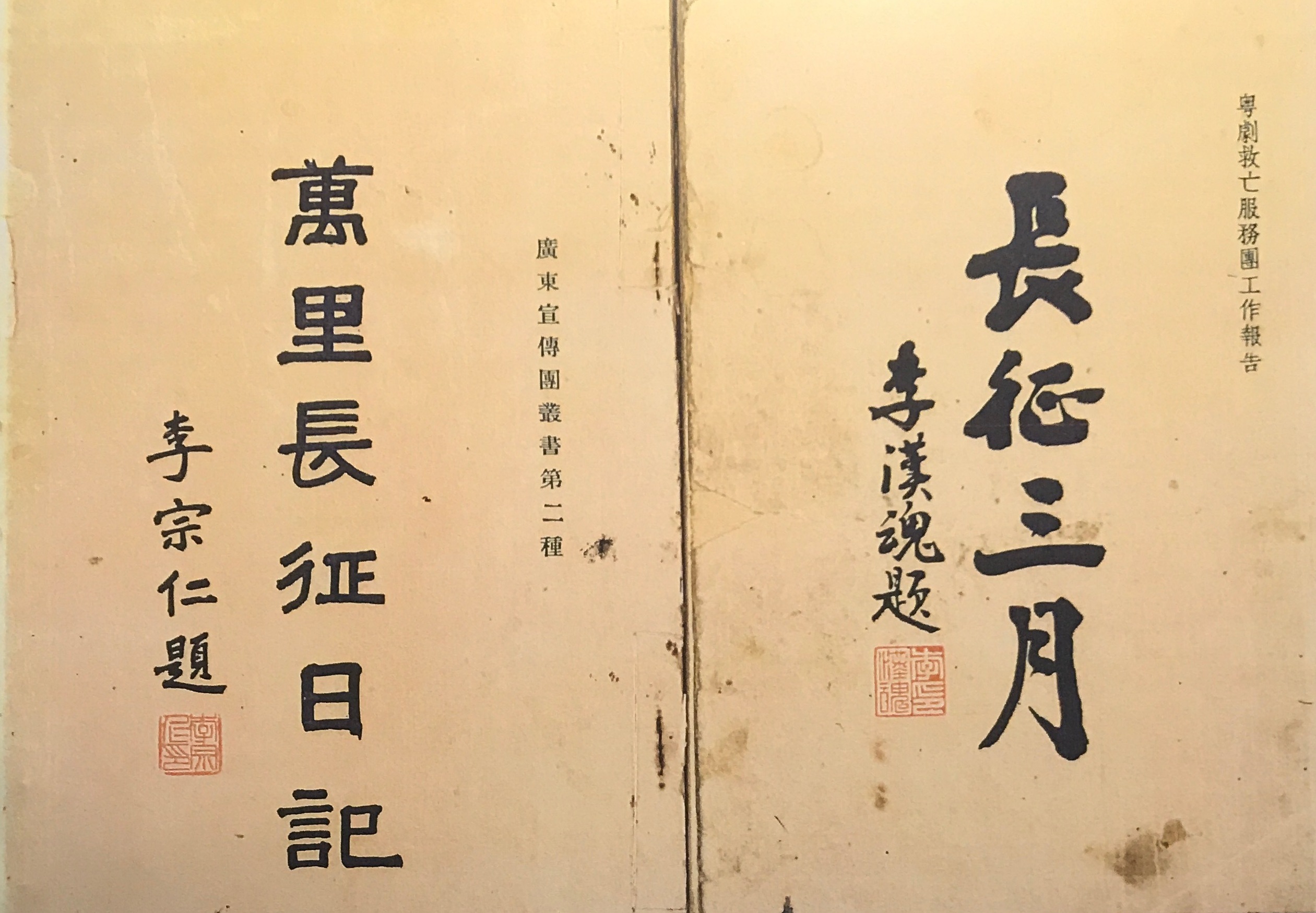
因為那時的戲壇中人說我那些戲太過硬了,不合時代需要,抗戰時的戲種已不受歡迎。那時流行的,好像《肉山藏妲己》等,演員穿着三點式衣服在台上咬水杯、扭腰、跳草裙舞的戲,我又不會演,亦不願演,真的是有些徬徨無計之感。
當日我和妻子住在那間產房,我的大兒子在美國檀香山的華僑家裏寄居;在菲律賓出世的女兒就在當地給一位福建人養育着;我的幼子和第三女兒,就寄居在越南西貢的一位福建人的家中,他是當地的一個當舖大王。這還不止,我的母親本來由我妹妹照顧的,豈料我的妹妹竟用二十元租了一個床位,把母親安置在石硤尾了事,我的家庭就是這樣分散着,自己雖知,但卻是無力將它團結在一起,心中的痛苦,實在難以形容。
後來多得我的師弟陳錦棠的幫助,藉他夫人的介紹,我得以到星加坡登台,我才稍為鬆了一口氣。
我剛才說過,人們非議我的戲不能追上時代,沙場之上因陋就簡,演出既沒有地氈舖地,亦沒有音樂節設備,戲服又因為沙塵滾滾,保養不善,破爛不堪;再加上我自問是守舊的人,沒有古何來有今,舊的劇目,始終是傳統的戲曲,仍有很多觀眾捧場。所以我始終拒絕演出所謂「新戲」或是放棄舊劇。
我由始至終都認為,作為一個藝人,是不應該被觀眾牽着鼻子走,而是帶領着觀眾。若觀眾要你行就行。要你走就走,藝人就變成了傀儡般,談不上什麼藝術表演了。我有權將古人孝悌忠信廉恥在台上表現出來,教育觀眾,成不成功先別說,但我以為這是我的責任。我一直持着這個態度去做事,從沒有改變過,黃飛鴻劇集就是因為這種思想而大受歡迎,而我的事業又攀上另一高峰,這些都是後話,暫且按下不談。
而我亦不怪當時的人,因為八年抗戰剛過,大家從苦難的歲月中回復過來,對於新的東西和容易吸收的東西,當然是趨之若鶩了,這是人之常情。
所謂「山窮水盡疑無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」,我終於得到機會。
我得到人的介紹,在「快樂世界」(現在飛機場)登台,演了七天戲,是一個海南人班主。
後來得到泰來棧老闆何道先生的襄助,借了四萬元戲服,使我得以赴星加坡登台。
(摘自《關德興自傳》,原載於香港時報1987年12月22日)


